一条路,不过千余米,却承载着一个民族昂首挺胸的记忆。河南漯河这条名叫“受降路”的街道,是全国唯一以“受降”命名的路。1200米长的街面,踩上去像踩着一本摊开的历史书,它的每一块砖、每一粒沙,都浸透着历史的重量,砖缝里藏着比教科书更鲜活的“胜利密码”——那是一个民族从屈辱里站起来的硬气。
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的,而是把苦难熬成钢的韧劲。胜利,不是命运的馈赠,而是抗争的回响。1945年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漯河被定为中原地区受降主会场。这不是偶然。这里曾经是日军屯兵据守之地,也是我们一寸山河一寸血、不屈不挠收复的失土。让侵略者在这里低头,让投降仪式在这里举行,让战犯在这里缴械——这不是报复,是公理;不是仇恨,是正义。9月20日那天,日军将领鹰森孝解下指挥刀时,亭外的百姓攥紧了拳头——这刀曾砍向同胞,此刻就得跪着交出来。战后,中国军队命令待遣日军拓宽取直原来的竹木街。败军之卒,俯首劳作,用残砖碎瓦铺就新路。老百姓站在路边,说不解气是假的,说痛快也是真的。老辈人说,让日军修路,是要他们“赔罪”,可这路修得再直,也直不过中国人十四年抗战里没弯过的腰。1931年到1945年,多少像漯河这样的中国城市被炸得稀烂,多少人揣着“打回去”的念想被埋进土里,才等到受降亭上“民族胜利”四个字刻进石碑。
记忆是最好的教科书,要带着温度传下去。受降亭曾被毁过,石碑也丢过,可漯河人没让它凉着。20世纪80年代挖着残碑时,老人摸着碑角掉眼泪;2012年复建时,商户们自发捐材料,学生们凑钱刻碑文。如今中州抗战纪念馆里,青灰色的碑和锈迹斑斑的步枪靠在一起,讲解员说“这砖是当年日军铺的”,孩子们伸手摸时,眼里闪的光,比霓虹灯亮。薛泮郎老人给孙辈讲“监督日军修路”,不是记仇,是怕忘了:太平日子是怎么来的,就该怎么护着。
烟火气里藏着新的胜利。路是无声的碑,碑是站立的路。今天的受降路早不是煤渣路了,走在受降路上,只见商铺林立、车流如织,早已没了烽火痕迹。卖胡辣汤的铺子挨着文具店,清晨的吆喝声混着学生的笑。可你站在复建的受降亭下看,会发现老街没变——当年铺砖的地方,如今走着背着书包的孩子,他们脚下的路宽了,可“不忘耻”的根扎得更深。但我们不能只是走过,而要读懂——读懂它砖缝中藏着的民族气节,读懂它命名时镌刻的国家尊严。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“历史是最好的老师”,漯河人把受降路走成了生活,也把记忆酿成了往前走的劲:街边的商户给抗战老兵送热汤,学校每年在受降亭前搞宣誓——不是要喊口号,是要让日子越红火、越记得是谁把这红火挣来的。
砖缝里的密码,说到底是“活着就得硬气”。受降路的砖早被踩得光滑,可每块砖都记得:胜利不是收一把指挥刀,是让后代不用再看别人脸色;不是修一条直路,是让中国的路想修多宽就修多宽。如今漯河的沙河边架起新桥,火车从受降路尽头呼啸而过,这是当年修路的日军想不到的——那个他们想欺负的民族,正带着记忆里的硬气,把日子过成了更亮的模样。
一个善于铭记的民族,才配拥有未来。“受降”二字,不是沉溺伤痛,而是清醒向前;不是延续仇恨,而是宣誓和平。正如复建的受降亭和三晋乡祠遗存,它们不是点缀风景的建筑,而是植入城市灵魂的记忆芯片。一旦激活,就是整个民族的共振。这些年,总有人以“忘记”为进步,以“放下”为豁达。但他们错了,真正的强大,从不是抛弃历史,而是扛起历史行走。漯河人坚持把“受降”刻在路牌上、写进地名里、融进日常中,正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。
我们从不渲染悲情,而是重申正义;不是延续旧怨,而是珍惜当下。让一条路、一座亭、一个名字,代代相传,不是为了记住仇恨,而是为了不忘来时路、走稳未来道。什么是“胜利密码”?它不是玄而又玄的谜题,它就写在这条路的砖石之间——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挺直的脊梁,在胜利时不改的清醒,在时间长河中不变的尊严。
这条路,叫受降路。这个民族,是中华民族。我们走过低谷,不曾跪倒;我们赢回光荣,不曾傲慢。我们修路、立亭、命名、铭记——不是为了活在历史中,而是为了让历史活在我们当中。正如碑文所刻:“愿后人鉴此,永固邦基。”这,或许就是漯河受降路给今天的启示——真正的胜利,永远属于那些记得来路、看清方向、步履不停的民族。(大河网特约评论员 邓随新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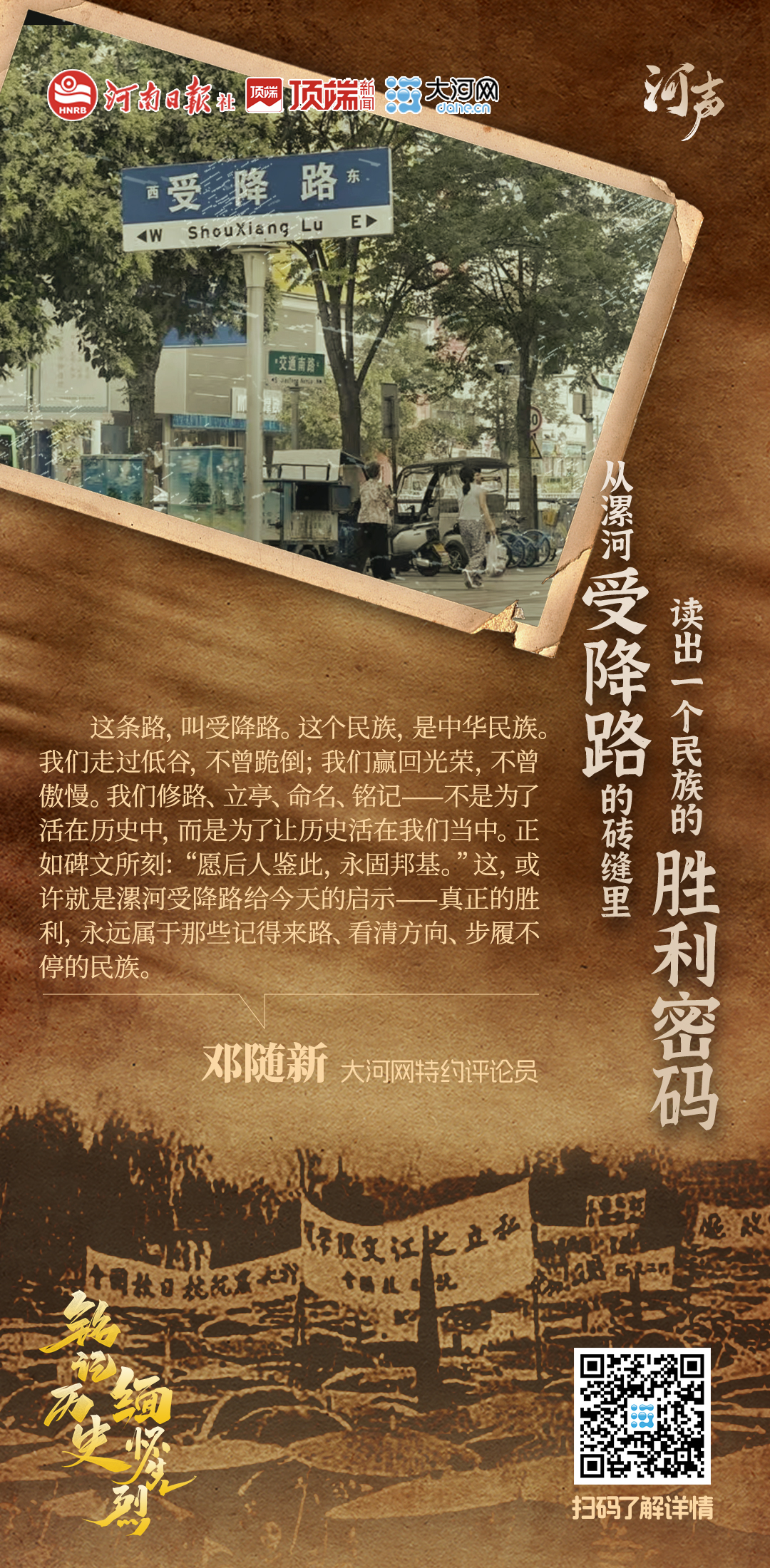
 首页
首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