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学校园里,电子围栏亮起红灯,家长群里不断弹出学生的课堂表现,成绩单跨越千里寄到父母手中,封闭式管理让学生足不出校园——这些场景听起来更像是中学的日常,却真实发生在当代高校里。近年来,一些高校的新校规屡屡引发社会对于高校管理“中学化”的讨论。当“禁锢式”教育成为热议话题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管理方式的争议,更是教育理念在时代浪潮中的艰难转身。
大学本应是青年与社会之间的过渡带:它既不同于中学的“全程监护”,也区别于社会的“完全放养”,其核心使命在于培育独立人格与自我管理能力。然而,当高校将早操、查寝、家长群等中学管理模式移植到大学校园,实质上是将成年学生重新推回“婴儿化”状态,仿佛其仍是需要“家长签字”的中学生。成绩单成了向家长汇报的“绩效表”,请假条沦为亲子关系的“遥控器”,当外在规训取代内在觉醒,所谓的“严管”不过是制造了“人在教室心在手机”的形式主义,甚至催生出“假性自律”的畸形生态。
大学生们抱怨被“圈养”,并非只是对自由受限的不满。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,他们本应是走向独立的探索者,却突然发现自己仍被无形的绳索束缚。这种束缚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,更刺痛了年轻人渴望自主成长的心灵。有学生调侃:“本以为上大学能像风筝一样乘风翱翔,没想到还攥在别人手中。” 大学本应是试错与成长的沃土,过度严格的管理却让这片土地失去了孕育创造力的空间。
高校教师的无奈同样值得理解。在教育实践中,他们目睹了部分学生因缺乏自律而荒废学业:熬夜打游戏错过考试,沉迷网络无心科研,甚至因自理能力差引发健康问题。面对这些现象,管理者试图用“中学化”的管理模式为学生兜底,出发点是对学生的关怀与责任。但这种做法,无疑是以成人的羽翼遮蔽风雨,却也让年轻的翅膀失去了搏击长空的机会。这种管理异化的背后,是多重社会焦虑的影射。当教育者把“防止堕落”置于“引导成长”之前,实际上是用消极防御取代了积极建构,这种思维惯性正在消解大学作为“人格主体”的本质功能。
这场争议的本质,是对“培养什么样的人”的深层思考。大学教育的核心,是帮助学生完成从“被管理者”到“自我管理者”的蜕变。过度保护式管理、“禁锢式”教育或许能在短期内维持秩序,却可能扼杀学生的独立精神与创新能力。真正的成长,往往发生在经历挫折、直面选择的过程中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:“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。”大学应该是学生在试错中积累经验、在自主中学会担当的舞台。
真正的大学精神亦当如未名湖水,既能映照天空的广阔,也能承载鱼儿的遨游。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中坚持“通才教育”,看似放任的学术自由反而培养出杨振宁、李政道等大师;德国洪堡大学倡导“孤独与自由”,看似疏离的管理方式却让黑格尔、爱因斯坦完成了划时代的思考。这些教育史上的明证提醒我们:教育者的智慧不在于编制多么严密的防护网,而在于营造让学生敢于试错、勇于担当的成长生态。
大学的围墙,不该是禁锢自由的屏障,而应是守护成长的边界。当我们把管理焦点从“行为纠偏”转向“人格养成”,从“严防死守”转向“价值引领”,当管理的温度与教育的智慧相遇,当约束的刚性与自主的弹性结合,我们才能培养出既有独立人格又有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。丢掉“奶嘴”,去掉枷锁,方能天高任鸟飞。这不仅是高校管理的课题,更是整个社会对教育本质的深刻反思与重新出发。(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张恒)
 首页
首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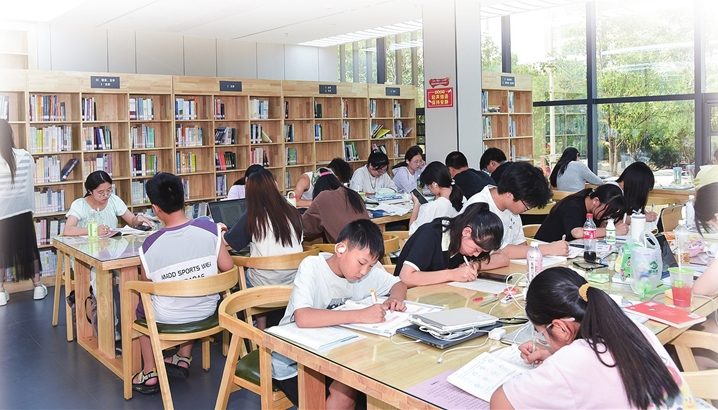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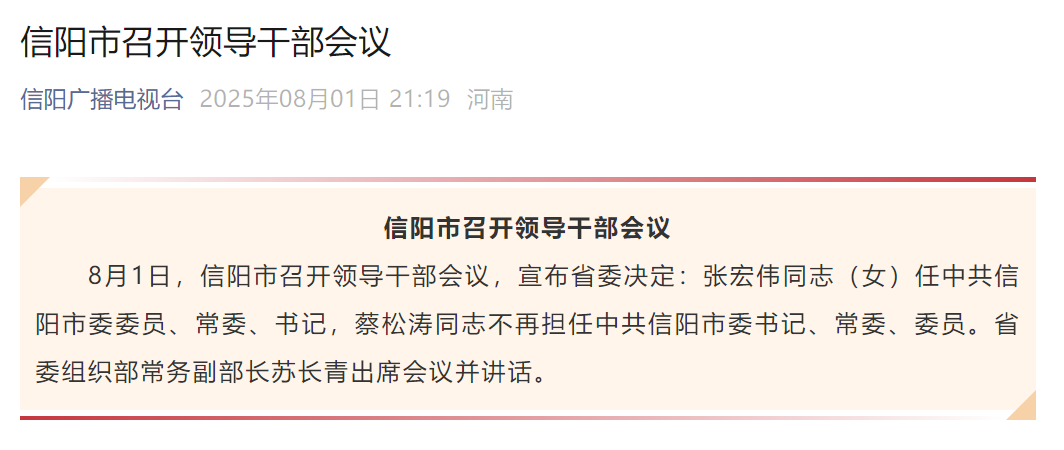






 豫公网安备 41010502003718号
豫公网安备 41010502003718号